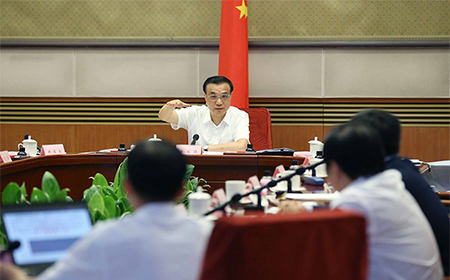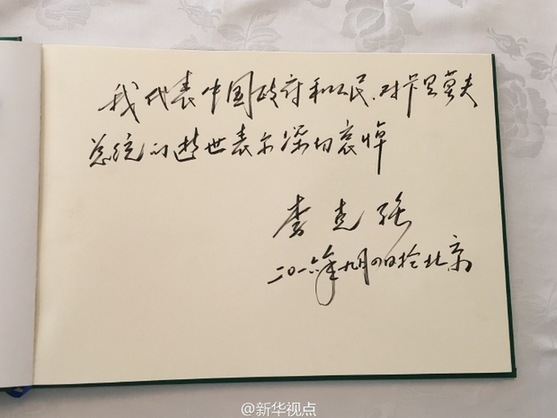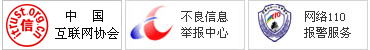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在涉及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上,多数作家、学者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产生了不少优秀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与此同时,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也在滋长蔓延,其主要表现是:“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只有彻底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才能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
一
文艺历来是社会思潮的晴雨表。自《苦恋》发表以来,36年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几乎渗透到文艺创作的一切方面。在此略举几例,稍作分析。
大凡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继承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宝贵遗产的基础上,经过28年的奋斗牺牲,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共和。然而,有的电视剧却指鹿为马,极力贬损孙中山、宋教仁等追求共和的先驱,而把慈禧、李鸿章、袁世凯这样顽固维护封建专制的人物描绘成为共和奠基的悲剧英雄,同时提示人们:时至今日,走向共和仍未成功。这不仅颠覆中国的近代史,也颠覆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对于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来说,革命是诞生新世界的分娩,因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但是“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还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很明显,如果只看到“死东西”、“废物”,而看不到“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则是在把握事物本质方面的一种倒错。然而,有的“文化”散文却无视近代革命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作用,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横加指责,甚至说这些革命对于中国经济的破坏比西方列强的侵略还要惨烈;有的小说则直接控诉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没有革命,“只剩下一堆‘暴力’”,由这样的革命所创建的政权也是“独裁和排他得可怕”。还诬称指引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直“把我们折腾得死去活来”。至于这个党的领袖毛泽东,则是一个靠《笑话大全》进行决策的玩笑家,像某些人“熟悉男女间的调情一样”,“熟悉怎样挑动群众斗群众”,“常常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我们说这样的小说“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一切,似乎并不过分。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有过失误,甚至有很严重的失误,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毕竟以举世罕见的速度发展,中国农村的面貌毕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人权状况、精神面貌毕竟不可与旧中国同日而语,这是新中国亿万农民每天都能感觉得到的事实。然而充满希望的新中国农村在个别作家笔下却变成了一个肮脏、恐怖、丑恶、混乱、荒诞的世界。这样的作家“用夸张、滑稽模仿加上变异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对50年来的宣传进行修正”,“令20世纪中国的残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向我们展示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从而“揭露了人类最黑暗的一面”。这些出自“颁奖辞”的评语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西方之所以奖励这样的作家,是因为这样的作家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农民以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描写,迎合了西方的政治需要。事实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创作领域虚无历史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恶搞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是红色历史的艺术再现,红色精神的载体,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基础。珍爱、保卫、传承本民族的经典,是世界上一切有出息民族的共同取向。然而,有的作家却无视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以一种极为轻薄的态度对红色经典进行肆意的篡改。流风所及,几乎没有一部红色经典能够幸免于祸。众所周知,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阿庆嫂,都是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形象,可是到了新编小说《沙家浜》那里,郭建光却成了品位低下、遇事窝囊的猥琐之徒,而阿庆嫂则成了一个卖弄风情的荡妇。郭建光、阿庆嫂与胡传魁的矛盾冲突,也不是爱国志士与卖国汉奸的斗争,而成了情色纠缠、争风吃醋的“三角”戏。
凡此种种轻佻和放纵,使文艺工作者在全国人民中蒙受耻辱,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蒙受耻辱。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来说,这是一种极具腐蚀性的负能量。
二
历史虚无主义反映到文艺研究领域,就是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艺史,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革命文艺史。比如,有的认为,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反封建等于反革命,所以作家们便由启蒙者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一耸人听闻的立论,显然是经不住事实的检验的。它不能解释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怎么会成为那么多追求民主的文艺青年向往的圣地,怎么能够让工农兵大众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革命文艺的主人公,怎么能够开创人民文艺的新纪元,怎么能够调动起“浩浩荡荡”和“千千万万”,最终掌握整个中国。事实上,随着“三三制”及“保障人权”等各项制度的落实,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不但经济上、政治上是民主的,文化上也是民主的。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从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中来,又到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中去的产物,集中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智慧和意志的产物。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深入考察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实践之后,曾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把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人民政权说成是一个“偏安的封建小朝廷”,丝毫无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形象,而只能暴露论者的刻薄偏见。
再如所谓“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其实,这并非“重写”论者的发明,而是拾取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牙慧。必须肯定,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然而,在这些“重写”论者那里,“重写文学史”并非一个严肃的科学命题。在他们看来,“构建”在“社会历史”基础上的文学史是“非文学史”,必须“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综观现代作家,大概没有一个是桃花源中人。既然如此,文艺的发展怎么能够脱离社会历史呢?“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五四以来的最大世情,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离开这一中国现代史的本质方面,一切文艺的发展变化都会变得不可理喻。比如,陈独秀为什么会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李大钊为什么要“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左翼文艺阵营为什么要发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五四运动之前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后期文明戏等等为什么会衰亡,赣南的山歌为什么在1927—1937年间如火如荼,延安的秧歌剧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繁荣,所有这些文意的变化、文体的兴废,离开革命史能够说得清么?客观事实是,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史的发展与革命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革命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催生新的文艺内容和形式,新的文艺内容和形式又反过来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把左翼文艺称为革命的“一翼”,毛泽东把革命文艺看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对于党和人民来说,革命文学史的教育与革命史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这里没有任何矫情、亏理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唐弢、王瑶、刘绶松等编写的几部新文学史或现代文学史,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基本上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原则,基本上实现了历史与艺术的统一。今天的学者重写文学史,应当在继承前辈宝贵遗产的基础上,把他们遗漏的方面弥补上,把他们失误的方面纠正过来,把他们未及深化的方面深入下去。如果全盘否定前辈的研究成果,甚至把他们坚持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也一起否定,就不仅否定了中国革命文学史,也否定了中国革命史。而由否定之火生成的灰烬拼凑起来的文学史,才是地地道道的“非文学史”。
否定革命文艺史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个:
一是唯启蒙论。在“否定”论者看来,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更是压倒了启蒙,于是向人民启蒙的作家便志不得酬、才不得展,革命文艺史自然也变得一塌糊涂。问题在于什么是启蒙?顾名思义,启蒙就是启智开蒙,让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自在的民族变成自为的民族。在一个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民族,启蒙的根本含义应是认清中国国情,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明确前进道路,以历史首创精神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这一本质性的启蒙,中国就永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一个灾难性的社会,其他一切启蒙,如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风俗、反对旧风俗,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之类都无从谈起。怎么能把救亡、革命与启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呢?即以论者认为受到革命束缚而不得启蒙的丁玲而论,其早期呼吁个人反抗压迫是启蒙,参加革命后弘扬集体反抗压迫也是启蒙,但是哪一种启蒙才具有现实性的品格呢?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其实,这种用启蒙否定救亡、否定革命的论调并非新鲜的东西,而是近80年前蒋廷黻的近代史观的翻版。在蒋廷黻看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能否赶上西洋,实现近代化。而要赶上西洋,就只能学习西洋而不能反抗西洋。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学习西洋就是启蒙,反抗西洋就是反对启蒙。一部中国近代史早已证明,蒋廷黻的近代史观是一种虚幻的史观,指引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打转转的史观,对侵略势力有好处、对中华民族没好处的史观。在中华民族已经独立了一个甲子以后,“否定”论者仍然坚持这种史观,不能说没有文艺以外的诉求。
二是唯个性论。在“否定”论者看来,作家一旦参加革命,一旦来到延安,一旦选择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就会导致个性泯灭,沦为工具,因而其创作也不可能具有任何积极的价值。什么是个性?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特定结构。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个性尤其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没有作家的个性,就没有风格,没有独特的审美发现,因而也就没有创作可言。然而,人的个性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它的培养和表现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群体、一定的社会实践。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不可能获得丰富的个性,更无从表现什么个性。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般地说,在具有历史先进性的集体中,一个人的集体共性(群体规范意识、责任意识、价值目标意识等)越强,他的个性(意志、品格、能力等等)内涵和表现也就越丰富、越强烈。欧阳山在早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生活领域的狭隘和无归属的彷徨,极大限制了他的个性发展和发挥,所以只能创作一些表现小资产阶级苦闷、感伤情调的作品。直至来到延安之后,仍然摆脱不掉因袭的重担,但是经过延安文艺整风之后,他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感召下,逐渐融入延安的大集体,融入延安的人民群众,融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洪流,于是他的集体共性日益增强,个性的发展也愈益充实、深沉和丰富,终于写出了深受党和广大群众称赞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和其早期作品《桃君的情人》《密斯红》等作一番比较,便不难看出:二者无论在思想深度、生活厚度还是艺术高度上,都是判若云泥的。大批作家成长的经历证明,革命队伍和革命实践,是作家培养健康个性的深厚沃土,扬厉创作个性的广阔舞台,实现个人价值的坚实阶梯,哪里会压抑、泯灭个性呢?著名诗人贺敬之说过,“不参加革命,我将不我”。其实,那些诬称革命作家失落个性的人,绝不是在尊重、维护作家的个性,而是要用另一群体的共性,一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相悖的共性来主宰作家。这当然是为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三是唯艺术论。在“否定”论者看来,鲁迅是“鲁祸”,茅盾的《子夜》是“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闻一多的爱国诗是诗人“狭隘性”的表现,赵树理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柳青的作品存在“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一言以蔽之,所有革命作家的作品,都不能称其为艺术。他们重写文学史,就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当然,文艺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自然具有不同于其他把握方式(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的特质,其中最基本的特质就是形式。一旦消解了形式,文艺便不成其为文艺。然而,一切文艺的形式都不可能成为一种孤立的存在。首先,艺术形式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比如抛开古代城市经济和市井生活,就无法解释词曲的产生和发展;其次,形式必须“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7页)作家对一定艺术形式的追求,也必然是对一定内容的追求;作家对世界的艺术把握,也必然蕴涵着对社会历史的把握。当然,有的作品可能以艺术胜,有的作品可能以内容胜,但是无论以哪一方为胜场,都不可能把另一方完全赶走。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文艺,唯艺术论恰如皇帝的新衣,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伪命题。即以夏志清认为文学成就高于鲁迅的张爱玲而论,在民族危亡、举国抗战的时候,她却在那里沉迷于“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傅雷评《倾城之恋》语),这难道不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倾向?在全国人民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时候,她却在《秧歌》《赤地之恋》中对人民中国极尽诬蔑毁谤之能事,这难道是纯艺术么?经过时光的洗涤,一切遮遮掩掩都已脱落,如今人们已经看得十分明白:“否定”论者否定革命作家的作品,绝不是因为这些作品缺失艺术,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这些作家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当然,我们不是说革命作家的作品完美无缺,也不是说因为那些作品内容进步就可以掩盖艺术上的缺陷,但是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毕竟是苍蝇。夏志清在艺术上是极力贬低丁玲而拔高张爱玲的,且不说丁玲在艺术上未必逊于张爱玲,退一步说,即便就是如此,丁玲也要比张爱玲高尚得多,因为她站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伟大斗争的潮头,是属于人民、讴歌人民的人民艺术家。
三
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泛滥,有其深刻的历史哲学根源和国际政治根源。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否定唯物史观的思潮也开始泛滥开来。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当推卡尔·波普尔和海登·怀特。
波普尔是英国学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魁首哈耶克的朋友。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最广泛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断,都强调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知识的增长极大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也无法预测。举凡历史的确定性、社会发展规律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正是从这种唯心史观出发,波普尔指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蓄意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在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灭亡并非不可避免,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缓和,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此后人类的历史任务不是革命,而是不断改良和发展民主。由此出发,波普尔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鼓吹历史的不可知论,一方面又预言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一方面反对历史的任何确定性,一方面又确定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仅此自相矛盾之处,就足以暴露这个披着现代科学外衣的学说的反科学本质,为国际资本张目的实用主义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40代起,波普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一样,一直影响甚微,甚至屡遭冷遇。直到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以后,才成为西方向第三世界极力兜售的“显学”。其命运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浮沉,足以证明它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武器。
海登·怀特是美国人,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的开创者。应当说,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对于纠正现代主义实证史学的机械性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对史家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完全脱离客观的抽象夸张,毕竟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和基础的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正是因为有了实践,才有了人的发展,有了历史,有了语言;有了历史、现在与未来的联系,有了人的意识、语言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实践赋予人类、历史和语言的统一性。然而,在怀特看来,历史却是一个杂乱、无序、矛盾、混沌的领域,没有任何统一性或普遍联系。是写作者的主观意识(思维方式、政治立场、伦理观念、审美倾向等)和特定解释(情节化解释、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赋予历史以联系、生命和意义。写作者的这一切主观因素,可以归结为语言,而且历史的叙述也必须以语言的形式出现,所以在历史写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不是历史,而是语言。这样一来,历史叙述也就没有真假、优劣的区别,而成了人们可以随意玩耍的语言游戏。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其《元史学》在中国出版时,怀特着意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史学家们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很明显,这是在鼓励中国的历史写作更加放纵写作者的主观意识。
有了以上简略分析,我们便可以归纳波普尔和怀特对于中国的特定影响:如果说波普尔颠覆人们对唯物史观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怀特则为人们随意涂改、编造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搞文艺的人不一定去读他们那些晦涩的著作,也不一定能懂他们那些玄虚的理论,但是通过理论界特别是高校某些专家的似懂不懂、似通不通的鼓噪,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唯物史观被波普尔推翻啦,以往的历史结论不对啦,文艺可以随便书写历史啦,如此等等。
历史是什么?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纽带,得以寄托心灵的港湾,得以自立的一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母体,得以开创未来的智慧和勇气的不竭源泉。国际资本要把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必须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而要摧毁这一切,就必须摧毁中国历史宫殿的一切建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核心建筑。关于这一点,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消亡”论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说得十分明白,即消亡非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于西方的历史。在这一旨在“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中,国际资本在国内买办势力的策应下,除了发动外部攻势和派人打进来以外,就是以大奖、资助、访问等等名目繁多的“实惠”诱惑一些作家、学者上钩。这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赛,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谁伪造的历史最符合国际资本的利益,谁获得的奖励、报酬也最多。
至此,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唯心主义史学观的渗透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形成来自后方的推力,那么国际资本的诱惑则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激励机制,形成来自前方的拉力。这样一推一拉,倘若正能量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那历史虚无主义能不愈演愈烈吗?
四
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保卫中国历史,保卫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保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已经成为坚持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要求。
必须坚持反对唯心主义与反对机械决定论的统一。在历史领域,机械决定论不承认偶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把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看作一条直线,把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当作按图索骥式的演绎推导;在文艺领域,机械决定论把文艺作品看作意识形态的简单传声筒,把复杂的极具精神个体性的艺术创造等同于机械式的生产。这些违背历史研究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的错误倾向,往往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名义大行其道,因而让后者的形象受到极大玷污和损害。其结果是让唯心主义抓住“把柄”,钻了空子,从而给予历史又一种更加深广的破坏。事实就是这样,机械决定论看上去好像是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东西,其实他们是兄弟,总是要一先一后地跑到前台来表现自己。只有把清理机械决定论和清理唯心主义的工作全都进行到底,才能剥夺它们相互依赖的依据,堵塞它们得以招摇过市的空间。当然,这两项工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当下的重点无疑是清理唯心主义。
必须坚持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多变多样,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这是无须回避的现实。给人以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既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所决定,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的必然要求。但是,自由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的社会实践。既然是社会实践,就必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既然离不开群体和社会,就必然要对群体和社会承担责任或义务,而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自我放纵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的自专。正如黑格尔所说:“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法哲学原理》第168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恶搞历史、抹黑历史绝不是学术或创作,而是对民族尊严、国家利益的肆意伤害,对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粗暴践踏。这好比踢足球,你无视比赛规则,不与队友配合,抱起足球横冲直撞,哪里还有踢球的自由?又好比过日子,你吃着自家的饭又砸着自家的锅,哪里还有全家人吃饭的自由?有必要对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提出告诫:既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么无论你怎样强调个人的思想自由,也不能逾越爱国主义的底线;无论你怎样翻滚腾挪,也不能侵犯国家民族的利益。在这个地球上,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在某些学者、作家视为自由天堂的美国,也绝不允许抹黑美国独立的历史,污辱华盛顿、林肯这样的领袖人物。2012年,恶搞林肯的电影《亚伯拉罕·林肯:吸血鬼猎人》刚一出笼,即遭到美国民众的“拍砖”。
必须坚持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艺创作,都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产生任何成果。即使是最严谨的史学著作,也会留下作者深刻的精神印记。对于以虚构见长的文艺创作来说,更是如此。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主体性不能离开客体性的依托,主观意识不能背离历史的真实。只有站稳尊重历史的立场,才能实现主客体的无垠融合,从而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正面的激发和表现。恰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有立足大地才有无穷的力量。前述那些抹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史的作家,由于其创作意图处处与历史的真实抵触、与人民群众的情感抵触,创作起来只好求助于生编硬造,于是文思不畅、笔下滞涩也就势所必然。请看他们的作品,那里除了概念化的政治宣泄,就是对于外国作家(如米兰·昆德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的拙劣模仿,哪里有什么戛戛独造、生气灌注的东西呢?
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来说,所谓坚持客体性,并不是要求作家像史家那样去追求历史事件、历史情节的真实,而是要求必须尊重历史本质的真实。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某些历史事件、历史情节上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真实,但是对历史的本质方面却作了扭曲的描写和评价,也不能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即使你对某些历史的描写,其事件、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正确反映了那一时代、那一时代特定阶级的本质方面,也可以说是尊重历史客体性的创作。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酣畅地描写杨开慧、柳直荀的忠魂飞升月宫的情景,这自然是游仙体的艺术虚构,然而却真实表现了人民革命的本质方面,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本质方面。可以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好比一个线段:一极是历史真实,一极是艺术虚构,这两极之间的广阔地带都是作家的用武之地。你可以往历史真实那里靠近,艺术虚构较少;也可以往艺术虚构那里靠近,历史真实较少。但是无论你选择哪一个点,都不能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重合。和历史真实一极重合,便成了历史学著作而非文艺作品;和艺术虚构一极重合,就会因违背历史本质真实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而你作出怎样的选择,表面看似乎取决于作家的个性,本质上却由其立场所决定。唯有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才能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也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作家要实现这样的统一,自己首先必须实现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文艺观的统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民作家,一个有前途的作家。
(作者:刘润为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来源:红旗文稿 摘自: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