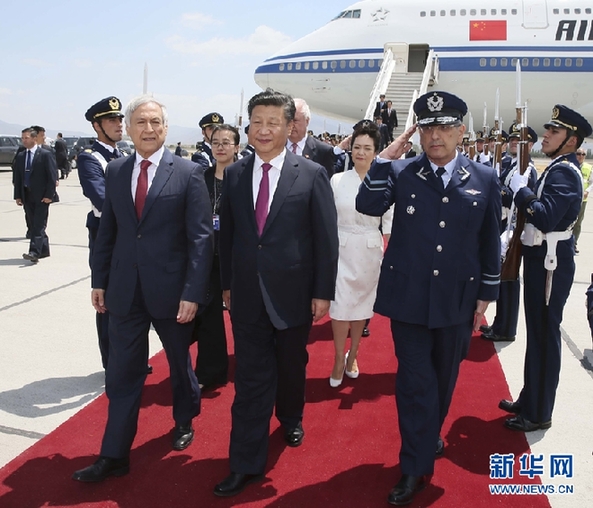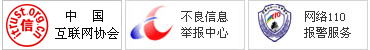高居翰
宋朝是中国绘画成熟的时代。宋前半期京城设在开封,是为北宋;1127年迁都杭州,此后是为南宋。极具独创性的有力画家接二连三地创作了许多为后世崇拜、模仿、叹为观止的杰作。这些人的作品存留到今天的并不多,然而就是以这仅有的几幅,也足以使我们相信,中国鉴赏家对他们的无上赞美的确是言有所据的。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与艺术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他们使用奇异的技巧,以达到恰当的绘画效果,但是他们从不纯以奇技感人;一种古典的自制力掌握了整个表现,不容流于滥情。艺术家好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来回应自然。他们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深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此时期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不朽名著,是画上署有范宽之款的一幅巨型山水。范宽是11世纪初大师。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我们觉得在自然界中无所不在,恰当而又和谐的秩序感。
范宽仅存作品 《溪山行旅图》 充分满足了以上这种赞美所引起的期待。布局雄伟、简单、肃穆、不炫耀雕虫小技,也没有任何其他矫揉做作的痕迹。它展现的境界是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主观或客观,写实或不写实,这些问题都不重要起来。画中的世界似乎既不忠实地反映物质宇宙,也不以人的了解来统御宇宙,而具有自身绝对的存在。一块巨嶂主宰着全景,幅度被丘顶的渺小树丛和建筑衬托得雄浑无比。从暗郁神秘的峡壁,冲流下一条白线似的瀑布。雾从山脚翻卷上来,飘流过山谷,隐约了山底,使陡壁看来格外高矗。笔触在细节部分越发显出它卓越的质量:线条,特别是勾勒树石峥嵘轮廓的部分,充斥了如电的力量。叶丛的形态由各个分别画成的树叶聚合而成。虽然画家消耗了无穷精力,成果却看不出什么斧凿之痕。石块和峭壁以“雨点皴”定型:无数淡墨小点叠落在岩面上,造成近于真实的层面效果。以上这些新画法,和在石块上累加灌木丛的主题,后来经常被“仿范宽”的山水画家们摹拟;这些技巧和主题以其最不矫揉的纯朴姿态出现在这里。画面几无人迹:只有两个渺小的人物正赶着骡队,一座桥,和半隐在树林后的寺庙,其余就是未经触及的大自然了。
郭熙的落款杰作 《早春图》,画于公元1072年,是现存唯一能在雄伟气势上与范宽并驾齐驱的作品。但是它的雄伟是一种不同的雄伟,是世界在不断变化中的骚动景象,而非对自然的永恒不变加以肯定。陆地的形式有意过分膨胀到圆肿的地步。它们相互融凝渗透,好像辽阔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强烈的不安定感激动着画面。一种忽粗忽细的线条紧张地颤抖着;似乎有一片不自然的光从底层泛起,照亮了石块;阴影在某个层面上神秘地折闪着;这些现象愈发使画面不稳定起来。而最不稳定的,是壁岩好像经历了万古的侵蚀似的,一律都从底部切开了。有些地方看来好像画家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原定计划。例如他把最右边,原本应该作为楼阁基地的坚稳的陆面,变成了危峻的悬谷,向下方开出一角隐蔽的世界,乍隐乍现。
近似幻像的地方如此之多;然而当我们更接近画面一步,探索画中被萦带的陆地和岩石所拱围出来的各个空间单元时———例如画面左边,坐落在风化了的河谷之上的景观;右边烟雾中的寺庙;左右下角,停泊着舟艇的两岸———我们发现某种程度的写实主义已经超过了前面提到的任何一张作品。郭熙把气氛透视法带入完美的境地。这种透视法使用逐渐淡化的颜色来描绘逐渐远去的景物,暗示了一种气氛正介入看画人和景物之间,以制造幻觉上的空间和距离感。烟岚在局部隐微了树顶。就像在范宽的 《溪山行旅图》 中一样,郭熙用荫蔽山脚的方法增加了山的高度。繁富的细节并没有削减构局的连贯性,这是此画绝妙处之一。虽然每棵蜘爪般的秃树都各具形态,它们重复出现之后,却成为一种打通全局的主题,同时也把庞大体积所造成的压迫感舒缓下来。
“马夏”派山水是西方人眼中最熟悉的中国山水,画派以两位创始人马远、夏珪之名而为名。马、夏和无数追随者创作了吸引力极为广泛而直接的作品,结果他们不但在本土获得盛名,就是在外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作品也深受着大家的喜爱。出自“马夏”追随者的数千幅画,还有马、夏亲笔制作的几件珍品,先被旅客和商人带到韩国和日本———仿品又再被仿,竟成为整个一种山水派的模本———以后又带到欧洲和美国,在欧美变成中国绘画的正统标准形象。
(摘自 《图说中国绘画史》,【美】高居翰著,李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者为已故美国学者,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