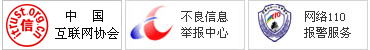从域外中国研究的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学和植根于欧洲东方学的传统汉学没有有效衔接,造成了当今西方世界存在“两个中国”的现象: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中国”与一个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在割裂而互不联系的方向上展开。
如今,中国正在从被描述的客体向主体转化,并由沉默的他者转为对话者。为了更好地与西人“对话”,我们有必要扮演“他者”的角色介入西方学术场域,打通“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研究区隔。为此,应对发掘新的概念、术语甚至议题,以更新角度、丰富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要从一个连续文明体存续和更新的角度出发,重塑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循此前进,或许可以找到一把理解中国的钥匙。
法国年鉴学派先驱布洛赫曾感慨:“我们对于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所以,他更看重“理解”。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利科解释:“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意即历史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但运用方法的终极目的是对历史的真正理解。近年来,有些学者任意夸大“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这既是对历史与现实缺乏“同情之理解”,又在研究上不仅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和令人信服的方法、手段,而且不具备建立在“史才”和“史学”基础之上的“史识”。类似片面的断章取义及随心所欲地作预设结论,是偏离“公正无私”的任意解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提“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例如,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从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这样的现代化研究话语有值得借鉴和肯定之处,但我们的学者不应被动追随和一味附和,而要学会在了解的基础上,与其展开平等“对话”乃至重新诠释。
二战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动”是一国现代化的关键。全盘西化与经济现代化的正相关性,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所验证,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同时,现代化应该是讲求生态文明的。一个尊重环境、尊重自身生态系统的现代化过程,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现代化目标和路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历史和国际环境变化,应当突出“传统”的重要性。传统是历史和国情的凝结与沉积,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却不能由人的意志随意否定,更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对世界上唯一保持了数千年活力之久的中华文明传统,我们更要注重挖掘其长期延续的内在动因。一句话,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要细之又细;对他人推销的各式“现代化改革”方略,要慎之又慎。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乔兆红